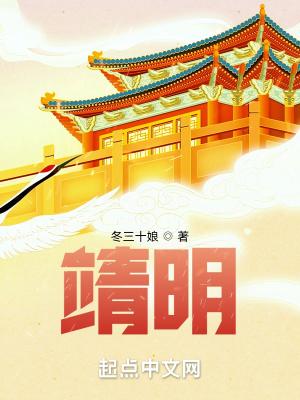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大唐之最强皇太孙 > 第2298章 拼凑(第2页)
第2298章 拼凑(第2页)
“那就让我来开这个头。”他站起身,面向殿外百官,“我,大唐皇太孙李承烨,正式向所有因‘理性规训’而遭受伤害的子民致歉。我承认,我们曾用科学的名义压制异见,用进步的口号掩盖不公,用统一的思想磨平差异。我们以为秩序高于一切,却忘了人心不可量化。”
殿内鸦雀无声。
三天后,朝廷发布《悔政诏》,宣布设立“国家反思日”,每年清明举行公开听证,邀请普通百姓讲述自己与体制之间的冲突故事;同时废除“忠诚度评分体系”,禁止任何机构以思想倾向为依据进行资源分配。
此举引发巨大争议。保守派称其为“动摇国本”,激进派则讥讽“道歉毫无意义”。但民间反应出乎意料地平静。许多人表示,他们并不需要皇帝低头,只需要一条不会因为说了真话就被切断的网线,一间可以自由发言而不被监听的教室,一个即使质疑也能活下去的空间。
而在岭南,“问答驿站”的纸条仍在不断涌入。有孩子问:“为什么老师说爱国最重要,但我爸说挣钱最重要?”有老人问:“我活了七十年,怎么越活越像外人?”还有一张涂鸦,画着一个大人牵着小孩的手,下面歪歪扭扭写着:“我想告诉我儿子,我不是坏人,我只是怕。”
小陈把这些都收好,定期寄往各地的“疑庐”分堂。她知道,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消失,也不应该消失。正如小禾曾在笔记中写道:“疑问不是病,它是呼吸。”
***
这一年冬天,敦煌学堂遭遇百年不遇的大雪。通往外界的道路全部封死,粮食告急。孩子们被困在校舍中,靠烧课桌取暖。那个曾带领同伴制作分光仪的小女孩??如今叫阿星??组织大家轮流讲故事抵御寒冷与恐惧。
轮到她时,她说起了小禾。
“她不是神仙,也不会飞。但她敢问别人不敢问的问题。她说,真正的勇敢不是不怕死,而是明知道会失败,还是愿意试一试。她说,文明就像一盏油灯,风越大,越要用手掌护住火焰,哪怕烫伤也别松手。”
孩子们静静听着,窗外风雪呼啸。
第二天清晨,雪停了。阳光照在结冰的沙地上,折射出七彩光芒。阿星带着几个学生爬上屋顶,用炭笔在积雪上写下巨大的三个字:“我们在。”
这句话被路过的飞鸟看见,被远处哨塔上的士兵望见,最终通过驿站传回长安。
皇太孙站在宫墙上读到这份讯息时,正握着一枚青铜铃铛??那是从余仲文旧宅搜出的原件,铃身刻着“鸣心”二字。他轻轻一摇,声音清越悠远,仿佛穿越时空,与那座南海孤岛上的火塘边滴水声遥相呼应。
他知道,这场变革远未结束。权力依然会腐化,谎言依旧会重生,新的“归真学会”也许正在某个角落悄然萌芽。但他也明白,只要还有人在问,在听,在记录,在为一句“我不懂”而羞愧或骄傲,那么光明就未曾真正熄灭。
他转身走入宫殿,命人起草一道新令:全国各县设立“沉默登记簿”,专门收录那些不愿发声却饱受压迫者的信息;所有政策出台前必须经过“孩童模拟测试”,即由十名不同背景的未成年人评估其可能带来的恐惧与希望;同时恢复古代“采诗官”制度,派遣专人行走乡野,采集民谣、俚语、梦话、疯言,作为施政参考。
有人劝他太过理想,他说:“如果我们连梦都不敢信,那现实还有什么值得守护?”
春天来临时,长安街头出现一幅奇特景象:一群孩子手持纸灯笼,上面写着各种问题,沿街游行。他们不喊口号,也不示威,只是安静地走着,灯光映照在行人脸上,如同星辰落入市井。
其中一盏灯上写着:“如果所有人都变成好人,坏人去了哪里?”
另一盏写着:“为什么大人们总说‘以后你就懂了’,可他们自己好像也没懂?”
最后一盏最小的灯笼,由一个五岁男孩提着,上面只有一句话:
“姐姐,你还在看吗?”
风起,灯火摇曳,照亮了整座城市。
没有人回答。
但所有人都知道,有些问题,本就不需要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