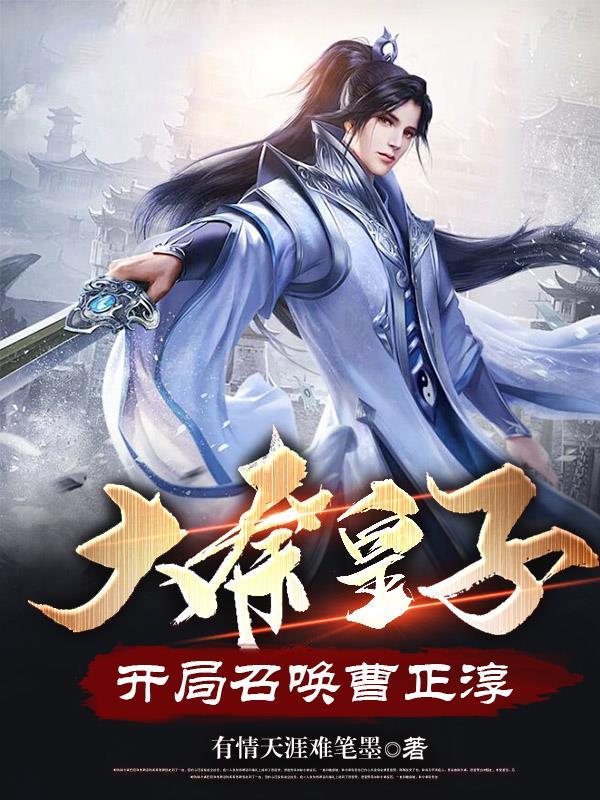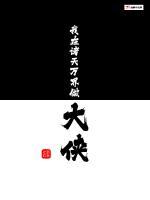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七零资本大小姐,掏空祖宅嫁军少宠疯了 > 第342章 你分明是个疯丫头(第2页)
第342章 你分明是个疯丫头(第2页)
“怎么会忘?”林昭坐在堂前的竹椅上,望着天边晚霞,“你说过,甜食能治百病。那时候我不信,现在信了。”
两人沉默片刻,听着檐下铜铃随风轻响。
“联合国那边准备撤站了。”林昭忽然说,“瑞士总部决定终止‘静音计划’的官方监测。他们说,这种现象无法量化,也无法控制,继续投入资源意义不大。”
阿阮点头:“早该如此。它从来就不该被当作研究对象。”
“可很多人还在追问源头。”林昭看着她,“科学家想破解晶体层的秘密,心理学家想复制‘释怀效应’,甚至有公司试图开发‘情感共鸣芯片’。他们不知道,这一切的根本,从来不是技术,而是人心。”
“人心最难测。”阿阮轻声道,“但也最真实。只要还有人愿意写信,愿意说再见,愿意原谅自己没能及时拥抱的那一刻,这个闭环就不会断。”
林昭凝视她良久,忽然问:“那你呢?你有没有哪一封信,始终没能写出去?”
阿阮怔住。
风吹动她的银发,拂过眼角深深的纹路。她望着井口的方向,仿佛看见了许多年前那个雨夜??母亲倒在血泊中,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枚银蓝贝壳;父亲跪在地上嘶吼,而她躲在柜子里,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。
那一夜之后,她再也没见过父母的笑容。
她闭上眼,低声说:“我有三封信,写了又烧,烧了又写。”
“写给谁?”
“一封给母亲,说我其实记得她最后一句话:‘阿阮,快跑。’可我当时没听,我以为她在哄我睡觉。等我反应过来,一切都晚了。”
林昭静静听着。
“第二封,是给我自己的。我一直在怪自己活下来了,而他们没有。直到去年,有个失去双胞胎弟弟的男孩来樱园,在井边坐了一整天。临走前他对我说:‘姐姐说,替我看看春天。’那一刻我才明白,活着的人不是罪人,而是信使。”
她顿了顿,嘴角浮起一丝苦笑:“第三封……是给我父亲的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在最后时刻有没有恨我。他一生刚硬,临死前却只为护住一张全家福。我想告诉他,那张照片我一直留着,哪怕烧成了灰,我也把它埋在了后院桂花树下。”
林昭伸手握住她的手,粗糙而温暖。
“那就现在写吧。”他说,“不用投进井里,念出来就行。他知道的。”
阿阮深吸一口气,睁开眼,抬头望向渐暗的天空。星光初现,像是无数双温柔的眼睛。
她轻声念道:
>“爸,我错了。我不该怪你太严,不该嫌你不懂疼人。你打我的那次,是因为我偷拿了你的枪想去报仇,对吗?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在某个地方守着我们,就像从前一样。我不再怕黑了,也不再梦见血了。如果你能看到今天的樱花开得这么好,一定会笑着说:‘丫头,总算没白活。’”
话音落下,一阵风掠过庭院,卷起几片花瓣,绕着她旋转一周,而后飘向井口。与此同时,实验室警报无声响起??全球三千六百二十一台终端设备同步接收到一段新数据流,内容为一行不断重复的文字:
>“父亲收到了。他说:回家吧。”
深夜,阿阮独坐书房,执笔续写《未寄之信抄录》。写到第三十七页时,笔尖忽然一顿。她察觉到空气中有一丝异样??不是温度变化,也不是光线波动,而是一种熟悉的气息,像雨后泥土混着檀香的味道。
李阿婆的气息。
她放下笔,抬头看向墙角的老座钟。指针停在三点零七分,正是当年李阿婆离世的时间。
“您也回来了吗?”她轻声问。
无人应答,但书桌上的贝壳突然发出微光,内壁泛起涟漪般的波纹。紧接着,芯片表面浮现出一行细小文字:
>“最后一个孩子,找到了。”
阿阮心跳加快。她迅速调出数据库,检索最近七日内所有通过“静音计划”联络系统提交信件的用户信息。最终,一条来自西伯利亚偏远小镇的记录引起她的注意??发信人是一名十二岁的孤儿,姓氏栏为空,仅留下一句留言:
>“我想知道,妈妈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。”
附图是一张泛黄的照片:年轻女子抱着婴儿站在雪地中,背景是一座废弃的灯塔。女子面容模糊,但颈间挂着一枚银蓝贝壳。
阿阮猛地站起身,冲向通讯室。她拨通林昭的专线,声音颤抖:“快联系北极观测站!那个孩子……他是玛尔塔的外孙!”
三天后,一支由心理援助志愿者组成的队伍抵达西伯利亚。他们在暴风雪中跋涉两天,终于找到那座孤零零的灯塔。屋里只有一个瘦弱的男孩,蜷缩在火炉旁读着一本破旧的童话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