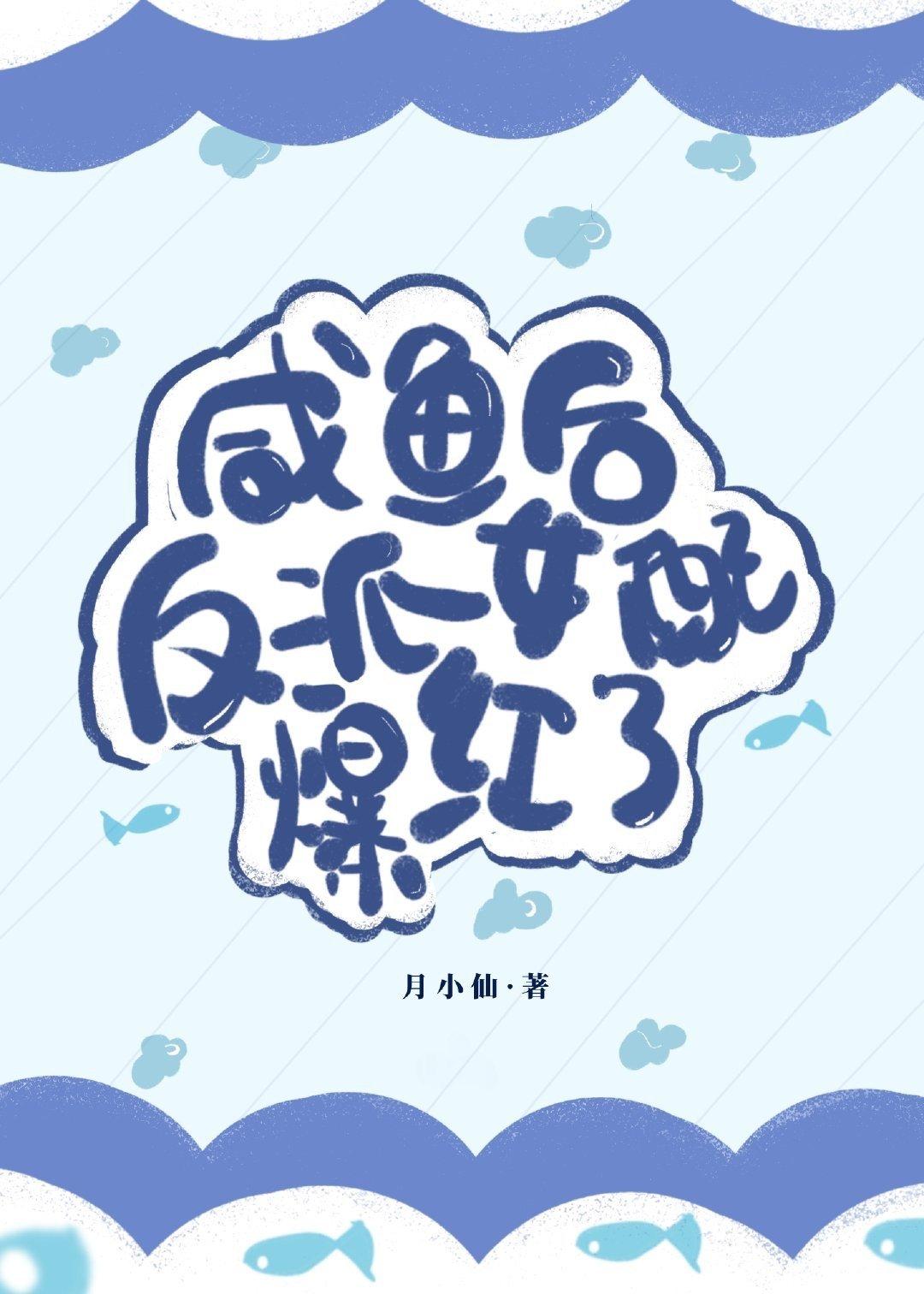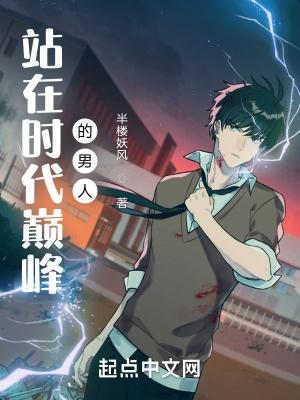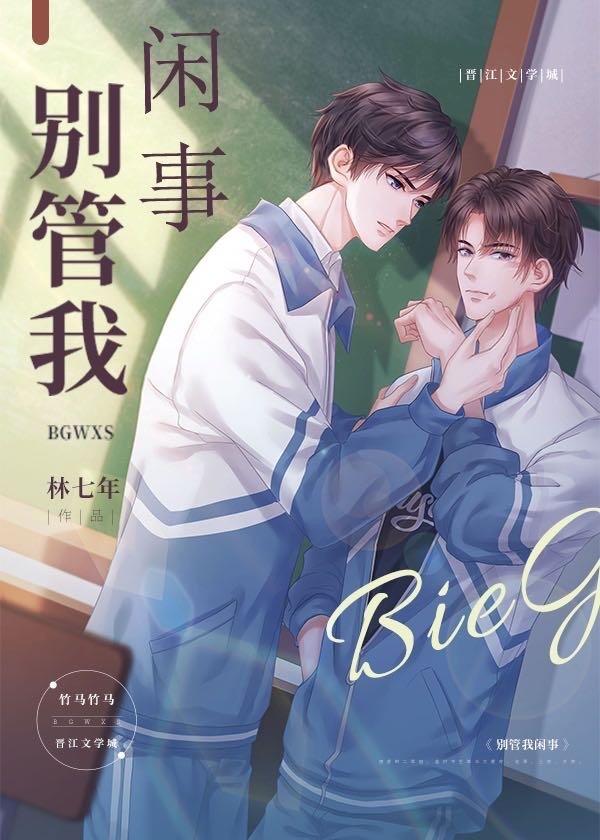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从采珠疍户开始无限就职 > 第62章 势同水火两相奈何(第1页)
第62章 势同水火两相奈何(第1页)
此言一出,满堂皆惊。
冯骁脸色大变,一把抓住那名士兵的衣领,厉声喝问道:“胡说八道!府衙大堂内外都有我们的人看守,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,几十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全都死了?你看清楚了没有!”
“。。。
夜风掠过青鳞崖,吹动老者衣角如残旗飘荡。他伫立良久,直至星辰偏移,那八字箴言悄然隐入云层,仿佛从未出现。可他知道,它已刻进天地律动的节拍里??就像林晚舟那一声啼哭,虽微弱,却足以震裂三百年的静默。
下山途中,苏挽在半道等候。她怀里抱着熟睡的女婴,脸上尚有泪痕未干。“老师,”她轻声道,“今夜启音灯第三次自燃了。前两次是红光,这一次……是金中带紫。”
老者脚步一顿。
启音灯颜色变化,自有记载以来仅发生过三次。第一次是三百年前伪契初立,灯火转黑,七日不灭;第二次是归墟裂口吞噬采珠舰队那夜,灯焰呈血赤之色,随后熄灭整整三年;而金紫交辉,则见于古卷《名册?异兆篇》中一句谶语:“**双色同燃,命定之人临世,旧誓将醒,新声欲出。**”
“她今晚唱过歌吗?”老者问。
苏挽摇头:“还太小,只会哭和咿呀。但……她在睡梦中哼了一声,像‘啊??’,又像某个音节的起调。我录了下来,用贝壳共振器试听,结果整排启蒙贝都亮了。”
老者伸手接过孩子,指尖轻抚其额。刹那间,怀中婴儿睫毛微颤,竟在无意识中张口,发出一个极短促的音:
“呜??”
声音不高,却让整座崖壁上的启音灯齐齐一晃,光芒骤缩再涨,如同呼吸。
“不是巧合。”老者低语,“她是‘音核’体质。”
苏挽倒吸一口冷气。所谓“音核”,乃传说中能承载万语而不溃散的灵魂根基,千百年难遇一人。上一个拥有此质者,正是三百年前那位率众反抗的林晚舟??那位最终投身归墟、以身祭誓的采珠女首领。据说她在沉没前最后一刻,曾以喉音震动海流,令方圆十里水脉逆涌三息。
“所以……这个名字,不只是象征?”苏挽声音发颤。
“更是召唤。”老者望向北方,“她们之间,隔着三百年的沉默,却由同一股意志牵引。那个女人临死前说‘梦见她’,或许并非幻觉??而是名字本身,在呼唤自己的继承者。”
月光下,林晚舟的小手忽然抬起,攥住老者的指节,一如初见时那般用力。这一回,他分明感到一股细微却清晰的震波从她体内传出,顺着血脉直抵心口,仿佛某种古老频率正在苏醒。
***
三年光阴如潮退去。
青鳞崖学堂已扩至十一层,最顶层专设“私语亭”原型舱??一间完全封闭的石室,内壁嵌满吸音海髓岩,中央悬一青铜铃,铃舌为空心,内置可焚稿的微型火槽。每日清晨,皆有渔民、织妇、退役忆述师前来倾诉:有人哭诉被律卫残余夺走田契的父亲至死未瞑目;有人坦白曾为活命举报同伴真名;更有孩童低声念着父母教他的禁忌童谣:“月亮船,载亡魂,穿归墟,唤旧神……”
话毕,稿纸投入铃心焚烧,灰烬随晨风散入大海。无人记录,无人评判,只求一句真心不被吞没。
与此同时,“盲录计划”悄然推进。十二名天生失明或幼年失明的少年被秘密召集,送往南溟孤岛训练。他们不学写字,只练听觉记忆与复诵精度。一名东洲来的少女,能在听完一段五分钟的独白后,逐字还原,连语气停顿分毫不差。她自称:“我的耳朵就是碑。”
而在北海,共语塔建设速度惊人。十七处分塔已有九座竣工,统音网络初步连通。官方广播日日播放“标准语教学节目”,声称要“净化方言杂质,提升沟通效率”。然而细心者发现,凡是节目中反复强调的词汇??如“服从”、“统一”、“感恩”??在日常对话中一旦偏离发音规范,街头语音矫正仪便会自动鸣响警告音。
更诡异的是,那首梦中歌谣开始蔓延。
西洲城一名接生婆在产后第七夜突然坐起,用陌生腔调吟唱:“万口同声,天下归心……”其夫惊醒制止,却发现她双眼翻白,嘴角含笑,无论拍打摇晃皆不停止,持续整整一个时辰才力竭昏厥。次日醒来,全然不知昨夜之事。
类似病例迅速增多。忆述师们联合调查,终于锁定源头:所有患者都曾在近期靠近过共语塔施工区域,且多数曾使用政府免费发放的“安心助眠香囊”??内填一种名为“静心苔”的粉末,据称可安神宁志。
苏挽带队取样化验,结果令人胆寒:静心苔实为深海共鸣藻研磨而成,这种生物本生于海底音脉交汇处,极易吸收并储存特定频率。而共语塔每日凌晨三点释放的低频声波,恰好能激活其潜伏效应,诱导大脑进入集体催眠状态。
“他们在用空气洗脑。”她在密报中写道,“不是强迫你说什么,而是让你以为自己想说这个。”
老者阅罢,久久不语。他翻开《名册?初卷》,只见那行稚嫩附注仍在,只是字迹似乎比三年前略显清晰了些,仿佛书写者正逐年长大,在时间之外执笔。
***
第七个春汛日,老者依约归来。
林晚舟已满七岁。
她坐在学堂后院的老榕树下,脚边摆着三十七个贝壳,每个对应一种濒危方言。三年来,苏挽与各地忆述师轮番授课,教她《安魂谣》的不同版本。此刻她正闭眼轻唱,嗓音清澈如泉滴石:
>“阿姆哟,莫怕黑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