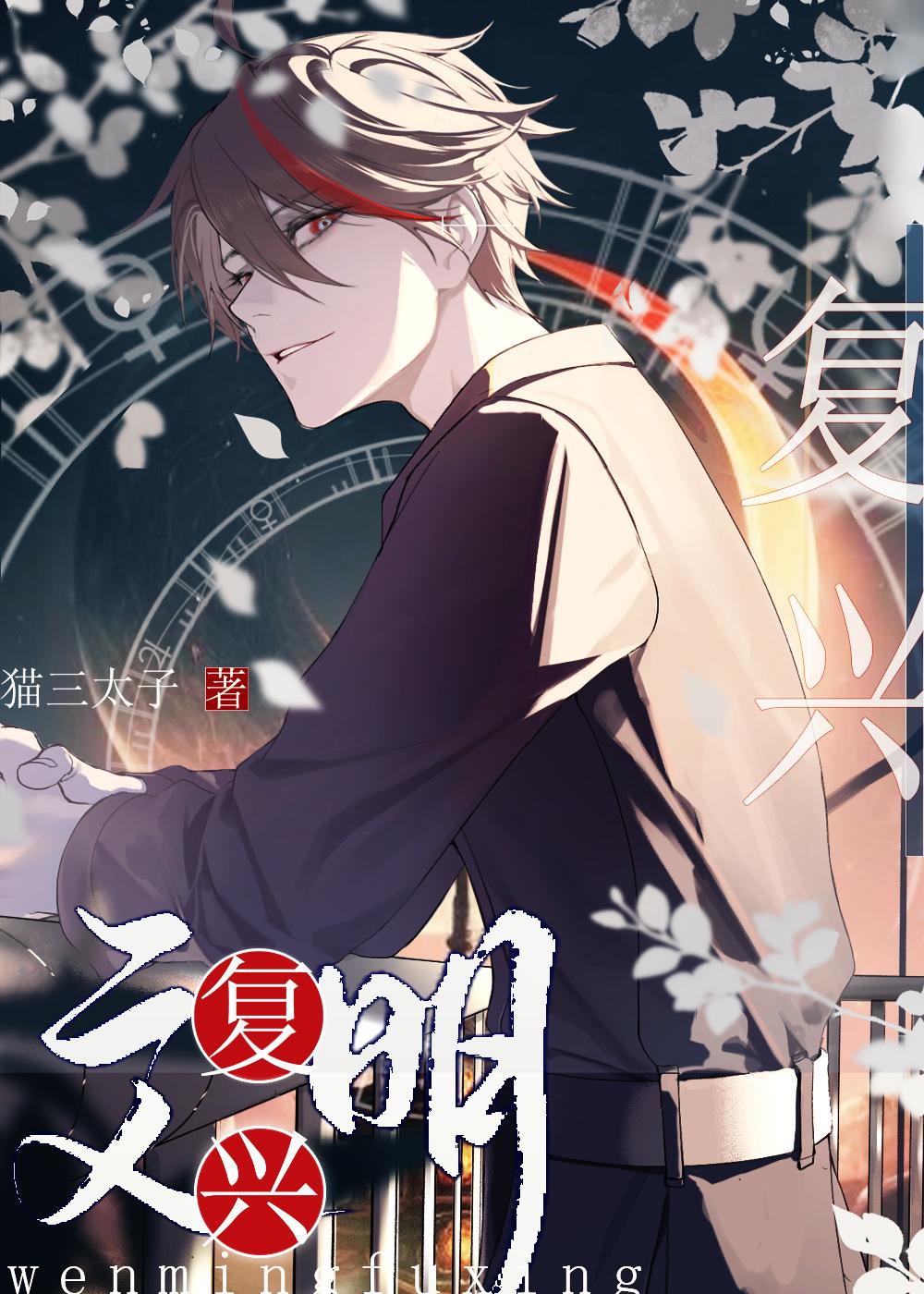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我才是徒弟们的随身老爷爷? > 第1章 蓝夜界(第1页)
第1章 蓝夜界(第1页)
与此同时,孙平正呻吟了一声,有些头疼地睁开了眼。
“真人总算是醒了!”
清脆的声音响起,孙平有些愣怔地望了过去。
是一个脸蛋红扑扑的姑娘,两条辫子挽成结,坠在耳后,红色的丝带顺着辫子。。。
山雨欲来时,天边总有一线光。
那不是闪电,也不是破晓的晨曦,而是无数细碎记忆在云层之上流转汇聚所形成的奇异辉芒。它如丝如缕,缠绕着风、水、火与人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,在将熄未熄之际,悄然点燃新的火种。
林小满站在西南群山之间的一座吊脚楼前,手中竹杖轻点青石板。十年行走,他的背已不再挺得笔直,眼角爬满了风霜刻下的纹路,可那双眼睛依旧清澈,像极了少年初遇《尘光集》时的模样。他抬头望着天空那道若隐若现的光带,低声呢喃:“又要变了。”
楼内传来琴声??不似骨琴清越,也不似铜钟浑厚,倒像是用整片竹林为弦,风吹叶响而成的天然律动。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盘腿坐在窗边,指尖抚过一排悬挂在屋檐下的竹管,每拨一下,便有一音落下,与远处传来的孩童诵读声应和成调。
“阿木。”林小满唤道。
男孩回头,脸上还沾着墨迹,显然是刚写完一页善录。“师父,您回来了?”
“嗯。”林小满走进屋,抖落肩头露水,“你昨夜又通宵记事了?”
阿木点头,从案上捧起一本新制的册子,封皮是山中老藤压制成的薄片,上面烫着三个字:《续光谱》。“我听村口王婆婆说,去年冬天,有个赶夜路的货郎摔断了腿,是李屠户背他走了十里山路送医,自己却落下风湿病根。这事没人报给‘忆光使’,但我记下来了。”
林小满接过书,翻开第一页,忽然瞳孔微缩。
纸页上的字迹正在缓缓泛金,如同被无形之手重新书写。原本只是简单记录的文字,竟自行延展成一段完整叙事:
>“癸卯年腊月十七,李大川冒雪负伤者赴医馆,途经三岭四坡,足陷冰窟而不弃。归家后高烧七日,邻里无人知其行。然其妻梦中见一白衣女子焚香叩拜,醒后于床头拾得一枚温润玉簪,非家中旧物。”
话音未落,窗外竹管忽自鸣一声,清音入耳,竟与《护心曲》第十五变奏的起始音完全契合。
林小满闭目良久,再睁眼时,眼中已有泪光。“这不是我在教你们记住善,”他轻声道,“是善,开始自己选择如何被记住。”
阿木怔住:“什么意思?”
“意思是……”林小满望向远方山谷,“有些故事,早已超越讲述本身。它们成了某种‘心印’,只要有人真心相信,便会自动浮现、生长、回应。就像当年我在戈壁捡到的陶片,就像南浔女孩看到的金文,就像老兵们面前升起的《戍边篇》??这些都不是人为所能及。”
正说着,楼下传来急促脚步声。一名背着药箱的少女冲进院子,发梢滴着雨水,脸色苍白。
“林爷爷!出事了!”她喘着气,“黑岩寨塌方,压住了三户人家!救援队还没赶到,村里人都慌了神,没人敢进去挖人!”
林小满起身就走,动作利落得不像个老人。阿木抓起竹琴追上去,少女则转身带路。
一路上,暴雨倾盆,山路泥泞难行。可越是靠近黑岩寨,耳边越能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??不是哭喊,不是呼救,而是一阵低沉却坚定的吟唱。
“……张二娘,丙子年救孤童三人,葬于东岗松林旁……
赵铁锤,丁丑年修桥不取分文,手裂血流仍不停……
陈瞎子,戊寅年夜巡防贼,杖毙悍匪保全村……”
那是几位老人围坐在废墟边缘,手持木牌,逐字念诵本村历代善人名录。他们的声音沙哑颤抖,却一字不差,仿佛这些名字早已刻进骨头里。
林小满驻足倾听,忽然明白过来:他们在唤醒集体的记忆。
这种记忆不是为了缅怀过去,而是为了激活当下??当人们想起“我们曾是谁”,他们就会变成“我们可以成为谁”。
他缓步上前,对众人道:“我们一起唱吧。”
没人问为什么,也没人质疑是否有效。一位白发老妪颤巍巍站起,开口便是《护心曲》第一段。第二句由阿木接上,第三句由药箱少女轻声续下。渐渐地,更多人加入,包括那些原本瑟缩在角落的村民。
歌声一起,奇迹发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