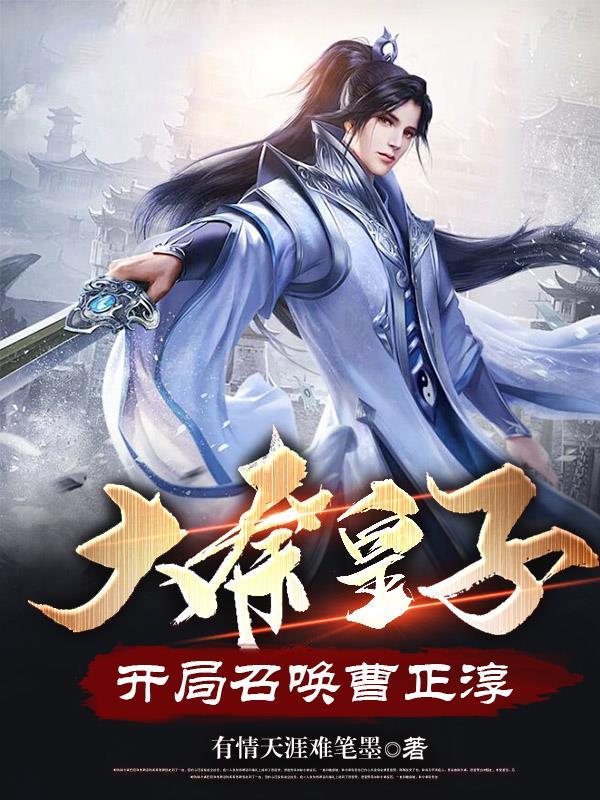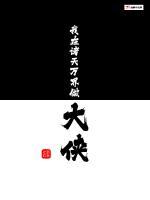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大唐:太平公主饲养指南 > 第四百八十九章 猴子捞月和新世界(第2页)
第四百八十九章 猴子捞月和新世界(第2页)
冬去春来,他又走过吐蕃边境、南诏丛林、安南湿地。每到一处,必做三事:讲授心学basics,救治病患,收集民间故事。他发现,最深刻的善念往往藏于最平凡的细节??母亲为孩子掖被角时的低语,农夫见蛇冬眠而不惊扰,书生拾金不昧后默默离去。
这些瞬间,皆被木鸟记录,转化为心网的能量节点。
两年后的秋天,他重返敦煌。
阿兰已在莫高窟外建起“守梦学院”,招收来自各国的学生,教授“梦境解析”“愿力传导”“集体意识共振”等课程。十万张儿童画拼成的巨幅壁画前,日夜有人静坐冥想,据说有些人能在入定时看见自己的前世片段,或未来的某个抉择路口。
“我们找到了新的传承方式。”阿兰迎他入殿,眼中含笑,“不再依赖单一继承者,而是培养群体觉醒。现在,全球已有七百二十三个‘共鸣点’,分布在六十四个国度。每个点都有一只木鸟驻守,或真或幻,或显或隐。”
裴景之点头:“很好。一人之力有限,万人之心无穷。”
当夜,二人共启“灵波解码仪”,尝试破译水晶颅骨遗留的最后一段加密信息。经过七十二小时不间断运算,终于解锁:
>“最终之门不在地理,而在人心。
>当千万人同时呼唤同一名字,
>空间将为之扭曲,时间将为之停顿。
>那一刻,死者可语,远者可近,
>死寂之地将开出花朵。
>条件唯二:
>一、纯粹无杂念;
>二、自愿献出心跳之一瞬。”
“这是……集体召唤仪式?”阿兰皱眉。
“更像是文明的紧急按钮。”裴景之沉声道,“只有在彻底绝望时才能启动。代价是,参与者必须真心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一部分??不是死亡,而是将自己最珍贵的一段记忆或情感献祭出去。”
两人沉默良久。
“你觉得,人类准备好了吗?”
裴景之望向窗外。夜空中,极光再现,蓝得纯粹,宛如太平当年裙裾的颜色。
“我不知道。但我相信,总有人会站出来。”
数日后,裴景之再度启程,目标长安。
归途比来时慢了许多,因为他不再独行。一路上,有学子追随,有医师同行,有工匠自愿打造可储存“心印”的玉简。他们组成一支小小的朝圣队伍,被称为“还愿者之列”。
消息传开,各地纷纷响应。有人寄来亲手绘制的木鸟图,附言“愿以此念助您前行”;有村庄集体抄写《心学箴言》,焚香送至驿站;甚至吐蕃赞普也遣使送来一匹雪白马驹,鞍上系着一条绣有“光明不灭”的藏毯。
第五年春,队伍抵达陇右。
此处曾是他初行时目睹饿殍遍野之地。如今田亩整齐,渠水潺潺,村舍炊烟袅袅。更令人动容的是,每户门前皆立一小碑,刻着“此饭曾有人饿死于此,今愿共享”字样。
“是我们的人做的。”一名随行青年告诉他,“去年,一群心学弟子来这里重建村落,发现旧驿道旁埋着十七具无名尸骨。他们挖出骸骨,一一安葬,并立碑为记。从此,无人再忍心浪费粮食。”
裴景之跪地叩首,泪流满面。
他知道,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,而是无数微小善念累积而成的奇迹。
终于,在第六年清明前夕,他望见长安城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