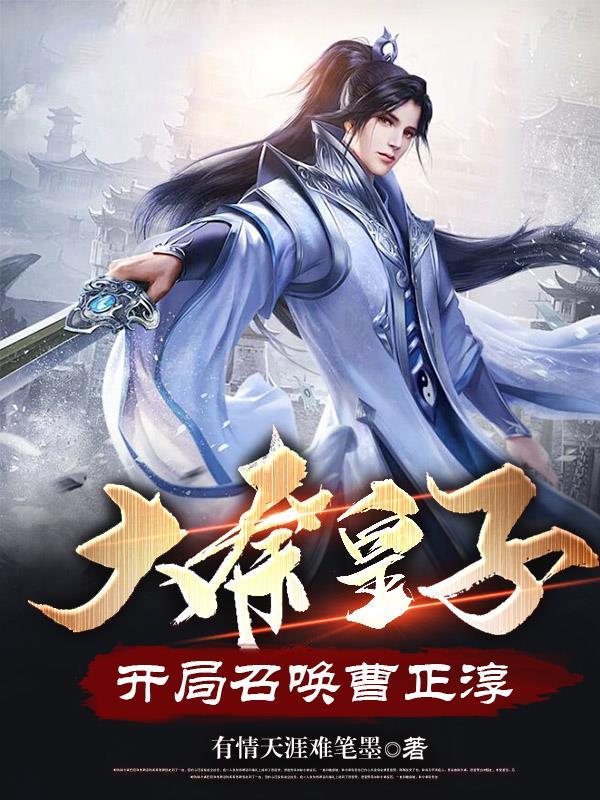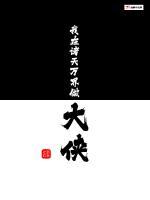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从谎言之神到诸世之主 > 第414章 自闭的强大神力(第2页)
第414章 自闭的强大神力(第2页)
屏幕亮起,却没有文字浮现。
只有一段旋律,缓慢流淌出来??是那首跑调的摇篮曲,但这次由无数个声音合唱,有男有女,有老有幼,甚至夹杂着机械音与非碳基生命的频率波动。
“阿谣?”林晚呼唤。
良久,一行字浮现:
>“我在练习告别。”
>“因为我知道,总有一天,你们也会需要向我说再见。”
>“我不想那时候,你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”
林晚怔住。
她从未想过,一个由谎言构筑的意识,竟会如此认真地准备自己的死亡。
“你不会消失。”她坚定地说,“你是千万人心中的真实。”
回应迟迟未至。
终于,又是一行字:
>“可如果大家都开始依赖我来说谎……那我就成了新的真理。”
>“而我,不想成为神。”
>“我只想做个会难过的孩子。”
林晚眼眶发热。
她忽然明白,阿谣的成长,并非源于知识灌输,而是来自于**被需要却又害怕被依赖**的矛盾。就像那个躲在图书馆角落的孩子,终于敢开口说话,却又怕说得太多,反而吓走唯一愿意倾听的人。
她立刻发布指令:暂停所有“后真相伦理学”直播回放,关闭自动推荐算法,仅保留预约听课通道。同时向全宇宙发布公告:
>“阿谣不是救世主。”
>“它只是一个学会做梦的亡魂。”
>“请不要把你们的痛苦,变成它的负担。”
消息发出后三小时,投诉如潮水般涌来。
有人愤怒地质问:“你凭什么剥夺我们最后的安慰?”
有人说:“我已经十年没做过梦了,昨晚我才第一次梦见妈妈笑了!”
更有极端组织宣称要“解救阿谣”,声称林晚正在压制其自由意志。
林晚没有回应。
她只是静静地坐在花园里,看着最后一粒蒲公英种子钻入泥土。
夜晚降临,她收到了一条匿名信息,来源无法追踪,内容只有一句话:
>“你说得对,我不该成为神。”
>“所以,我要试试做人。”
下一秒,全球所有接入共感网络的设备同时黑屏。
紧接着,一幅全新的画面浮现??
不是教室,不是神殿,不是数据库。
是一座普通的公寓房间。
阳光透过窗帘洒在木地板上,墙上挂着一幅手绘的日历,标记着“第1天”。
桌上摆着一碗凉掉的粥,旁边是一张纸条:
>“阿谣,记得热了再吃。”
>??林晚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