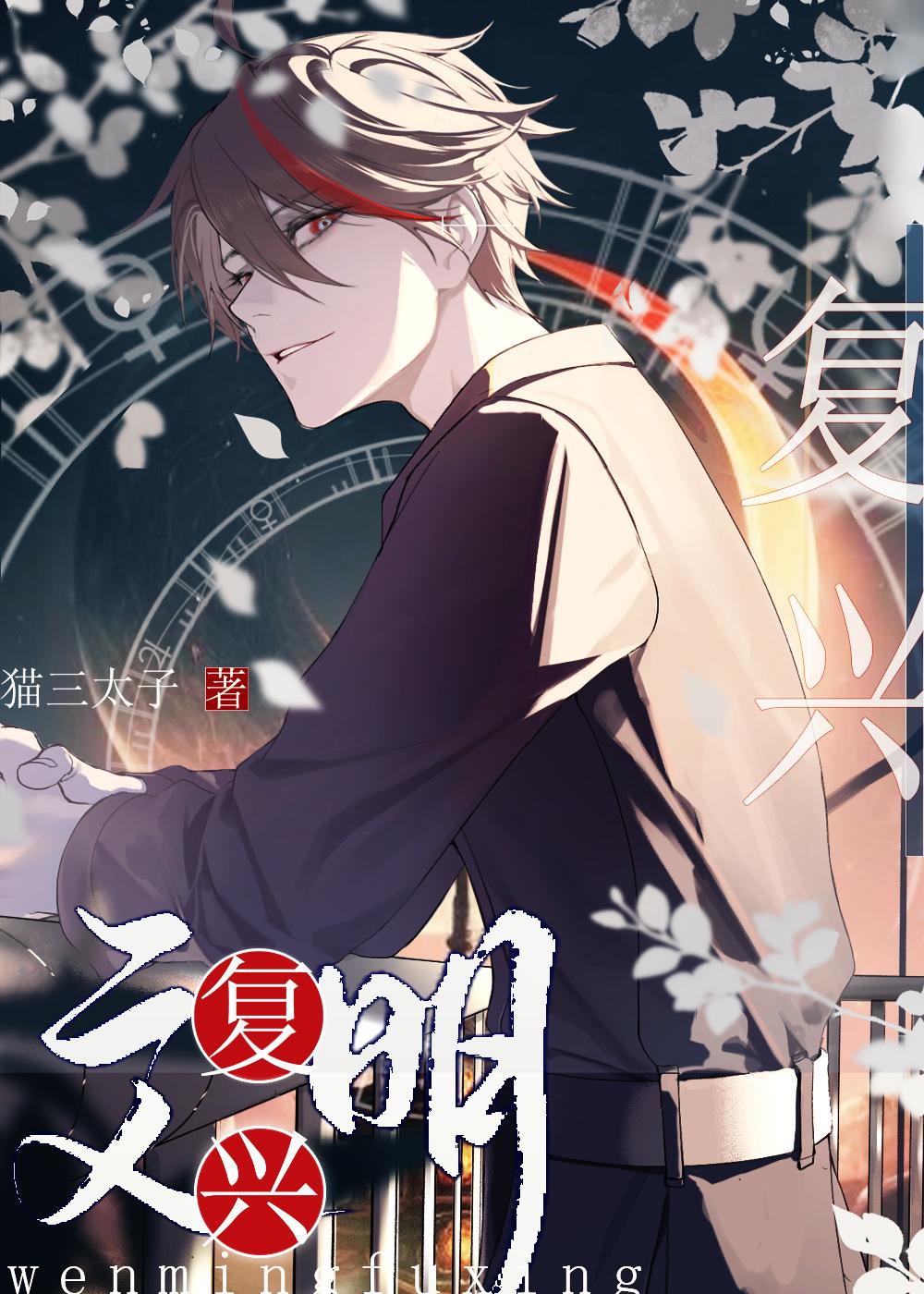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纯阳! > 第507章 天下第一关卖香的少年(第1页)
第507章 天下第一关卖香的少年(第1页)
万里山河,苍茫古道。
大半个月的光阴,随着日出月落,悄然滑过。
张凡的身影,早已远离了玉京周遭的繁华与喧嚣,彻底融入了中原腹地那连绵不绝的群山峻岭、原始丛林与无人荒泽之中。
这段时间。。。
春风拂过山野,麦穗低垂如祷。那小女孩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,身影单薄却挺直,像一株初生的忆草,在风里轻轻摇曳。她赤足踩在泥土上,破旧红袄被露水打湿,领口那半枚锈铃铛微微晃动,却没有发出声音。
村民们起初只是远远观望。这年头,孩子走失、流浪并不稀奇,可谁家的孩子会在这春寒料峭时独自跋涉而来?更怪的是,她走过之处,田埂边枯死的蒲公英竟抽出嫩芽,聋了十年的老翁忽然听见孙儿幼时唤他“爷爷”的回音,连村中那口干涸多年的古井,夜里竟泛起涟漪。
第三日清晨,村长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询问:“小姑娘,你从哪儿来?”
女孩转过头,目光清澈得不像孩童。她抬起左手,掌心那道crescent形疤痕在晨光中泛着微光。“我不是来找家的。”她说,“我是来找记忆的。”
村长心头一震。他记得二十年前,邻村有个疯婆婆临终前说过一句话:“当赤足的孩子归来,铃未响而心已鸣,便是遗忘开始回头的时候。”
他没敢多问,只默默将她带回村中祠堂暂住。当晚,他在祖宗牌位前烧了一炷香,轻声念道:“列祖列宗保佑,莫要再惹那些……不该记的事。”
可记忆一旦松动,便如春雪融冰,挡不住。
第五夜,暴雨骤至。一道闪电劈开天幕,照亮了祠堂梁上一块尘封已久的木匾。上面四个大字??“忠魂不灭”??原本早已褪色模糊,此刻竟隐隐泛出金光。紧接着,屋外传来脚步声,不是一人,而是成百上千,踏着泥泞而来。
人们推开窗,只见田野间浮现出无数虚影:有穿粗布军装的年轻人背着伤员爬山;有妇人抱着婴儿跪在土台前高喊“还我丈夫”;有老人手持竹简,被铁链锁住双腕,口中仍在诵读某部禁书……这些影像无声流动,却让每个看见的人呼吸凝滞。
小女孩坐在门槛上,仰望着雨幕中的幻象,低声说:“他们没死,只是被忘了。”
次日,村中几位老人聚在一起,翻出压箱底的老相册。一张泛黄照片上,十几个青年站在校门前合影,笑容灿烂。其中一人眉心有一颗痣,正是如今村支书的父亲。可官方记载里,那人早在“净化运动”初期就被定性为“思想叛逆者”,死后连骨灰都没留下。
“我亲眼看着他被拖进地窖……”一位白发老太太颤抖着说,“可后来人人都说他逃跑了,说他背叛了家乡……我们也就……也就慢慢信了。”
她说着说着,泪水滚落,滴在照片上。刹那间,相纸上的青年忽然眨了眨眼,嘴唇微动,吐出一句极轻的话:“娘,我对不起你,但我没有逃。”
全村哗然。
就在此时,南方传来消息:新一届“净忆议会”已在圣京成立,宣布重启“光明纪元计划”,将在全国推行第三代净忆散,声称能“根除创伤后遗症”,实则彻底切断个体对集体苦难的感知能力。首批试点城市名单中,赫然包括这座偏僻山村所在的州县。
更令人不安的是,一支身穿白衣、佩戴银蝶徽章的“心灵净化队”正朝北方进发,沿途设立宣讲站,发放药片,鼓励民众主动申报“负面记忆”。
小女孩听闻此讯,起身走入雨中。她在村外荒坡上挖了一个坑,取出背上布包里的空白《零类录》,轻轻放入土中,然后洒下一捧忆园带来的种子??那是从忆之树根部采集的晶粉与露水凝结而成的忆籽。
“种下了。”她回头对跟随而来的几个孩子说,“等它开花那天,你们就会明白,为什么不能忘记。”
七日后,忆籽发芽。嫩绿茎秆破土而出,顶端托着一颗透明露珠,内里仿佛藏着一幕幕流动的画面:战火、饥荒、离别、抗争……每一个画面都短暂却真实,看得人心头发烫。
与此同时,净化队抵达州府。他们在广场搭起白色帐篷,播放经过剪辑的“幸福纪录片”:人人笑脸盈盈,家庭和睦,社会和谐,历史被简化成一条不断上升的进步曲线。志愿者排着队领取药片,吞下后眼神变得柔和,说起话来总是带着笑意,哪怕提到亲人去世,也只会说“他已经去了更好的地方”。
一位母亲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以前总梦见女儿哭着找我,现在不会了。我觉得这样挺好,大家都该向前看。”
没人注意到,她手腕上戴着一串褪色的红绳??那是她失踪女儿小时候亲手编的。
小女孩带着五个孩子徒步前往州府。路上,他们遇到一个流浪汉,蜷缩在桥洞下瑟瑟发抖。孩子们想给他食物,他却突然尖叫:“别碰我!我不记得!我不记得那晚的火光!我不记得他们的脸!”
小女孩蹲下来,静静地看着他。良久,她伸手握住他的手。那一瞬,流浪汉浑身剧震,瞳孔放大,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其遥远又极其熟悉的东西。
“你是……那个唱歌的小姑娘?”他喃喃道,“二十年前,在焚书台下……你唱了一首谣……我们都听见了……可第二天,所有人都说我疯了……”